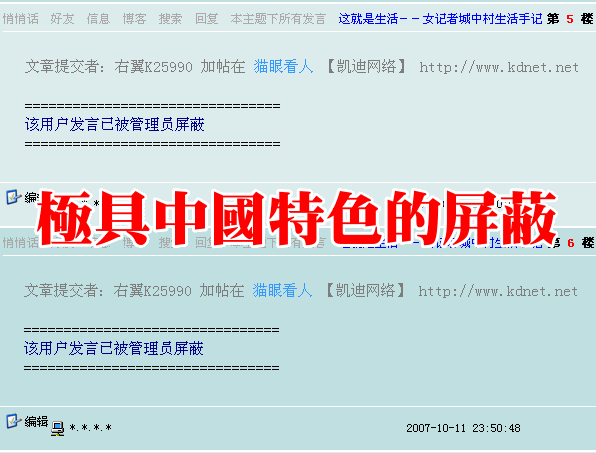當今民建聯學懂把德生先(民主主義)跨跨其談,內地高舉賽先生(科學主義)發展作為綱領,如此種種,是魯迅一代人始料未及的。事實上,五四運動隔了許多突兀的時光,如林毓生曾談及在大躍進中地理科學家錢學森「以對太陽黑子的解釋,來為毛澤東違反自然規律的、每畝年產量的瘋狂估計,提供科學的解釋」,直到現今被定性為一場「愛國運動」。九十年歲月已是九重山,五四一詞背起的意象太過沉重,似是不再激得起漣漪。
斷斷續續,雖然這種以「全盤西化」之名來挑戰國家時政的傳統得到「繼承」(同時惹得外國勢力干預、漢奸之美名),然而在國家也懂得挪用些西方概念,說科學有些科學說民主有些民主,新聲亦變成了老調子之際,餘下的問題是:在90年後,我們要推進一種什麼的五四精神於這片中國/香港時空呢﹖
重建中國時空 回到魯迅的時代,他各種話語所隱含的政治地理實踐,其實主要是透過用西方的思想/文化建立一片全新的想像領域,從而介入當時腐朽的中國社會文化問題。毛澤東也曾說過19世紀後的中國一直都是「向西方找真理」。封建後,中國的國髓主義仍然興盛,如老樹盤根一樣保守,被魯迅認為是拖著後腿不能進步的原因。要徹底的批判,最直接的方法當然就是與國髓全然的割裂,即「全盤西化」,質疑中國人甚至是知識分子的猶抱琵琶,「究竟這些文化,對人民生活到底有什麼益處呢﹖」故此,西化理念都與什麼二元化、對立了傳統與現代這一類當代學術甘之如飴的流行話題無關宏旨,此實關乎知識的政治 (politics of knowledge) ,是嘗試在一面紅旗都是因循國髓的情況下提倡西化理念,「建立西洋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開拓媒體空間(我手寫我口)、社會空間(反對三綱五常)、政治空間 (民主/權利觀),試圖激起具號召力的運動希望。
在特定時空引入西方理念來討論社會問題固然具政治性,然而五四背後這種對時空觀念本身的重建,我認為就是五四運動裡面最具影響力的精華。
試想像一下,一覺醒來,你被告訴原來中國的時間(歷史)絕非牢不可破的,可選要或拒絕它 (或者如魯迅建議,無謂需要對過去有任何奢望)。這對當時封建後仍然將會周而復始的中國時間,是多麼當頭捧喝的一擊﹗魯迅所使用的大抵是啟蒙式的進步時間觀,直線的,有前無後,never look back,明顯是一種掌握當時中國時間的局限性而刻意安置、建立相互對抗的技藝。
除了為時間建立如箭在弦的張力,重塑空間形式亦是重要的一環。在上文提及對不同類型新空間作大幅度的開闢之外,在魯迅筆下,甚至是長城這往往被提升為神聖的空間,也可以想像如何改造/咀咒它。他曾以這樣爆破的方式「毀壞」中國既有如鐵房子般的空間想像,被問:
「假如是一間鐵房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壞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答曰: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故此,這種全盤西化傾向的主義,精髓不在於「全盤西化」本身,而是在於透過倡議一種「以外」的領域,對中國社會的時間與空間觀念重塑之、拉闊之(當中必然涉及破壞),從而使一潭死水的民初在各方面建立非封閉式的未來。
如此的話,這種「衝擊時空」的五四精神便變成了可攜帶的(portable),多於Edward Said所言在地域含義上的理論在旅遊(theory travels),而恰如莊子說,我們從此可帶它縱橫時空。
衝擊與無聲 當此理解縱橫到香港,便容許了我們察覺到各種與「衝擊時空」一脈相承的實踐。例如本土行動對本土這空間尺度的建立,正好面向著一直以來香港在被宗主國之間把玩、同時在自號要追求國際化大都會這種既強調國家又強調國際卻從沒有本土的虛無尺度想像,打破了不少香港人仍然停留著國際化的無奈瑕想。透過這樣引入新空間的光譜,來打開各種對身份、城市等懸而未決的問題思考及實踐的空間。
是故,我們看到全力反對國髓派保留舊物,曾說過「要我們保留國髓,也須國髓能保存我們」的魯迅,也能被朱凱迪批評因循貪吃空間的土地發展邏輯的市建局乃「吃人的保育」所傳承。是故,歷史學人周思中在前文爭論呂大樂抹殺了70年代青年人爆發力的定形時間觀,也顯現出了五四動搖時刻的英魂。
從前我們面對殖民化,現在卻正面臨強大無比的全面國家化。無可否認,香港的時空已經在近年被「上面」充分的定義——空間上香港與深圳已(被)計劃「同城化」,廣深港高鐵與各種措施的配套,勢要將整個珠三角統一起來。這些計劃令人驚愕之處,不在於經濟上如何分工配合、基建上如何加強接駁等,而在於我們的生活模式也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被規劃」,未來要在區內規劃多少小時的生活圈、誰應在那裡生活、生活方式應該如何等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問題,它是最貼身的交碰,是未有充分參與底下首次來港的社會主義規劃。
面對生活模式將要被政權由上而下地改造,當然有人會叫大家不用驚訝,嘗試降溫,情況類似呂大樂早前以「新思維網絡」之名所提出的,把二○四七年的香港鎖定成一種無可避免的、必然與珠三角融合的統一空間形式。這是個封閉、預設的未來。按文章理解,現在與以往什麼追求都可以忘記,最重要是思考(我懷疑這樣是否還能稱之為思考)我們「如何充分運用區域融合和合作所釋出的力量」。這種放棄任何對當下時間與空間的爭議,純粹謀求一種未來被定義下折衝又折衝後的恩賜,正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亦是普遍香港人只懂移民、沈默與選擇性遺忘的症候。
新青年們,常常說我們都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若然是維持現況,我想到五四的一百週年也是如此。你是否願意接棒,為這世代納喊出一種新的時間與空間﹖